我的老家地处湘西北丘陵地区,在我的童年时代,妈妈在煤油灯下扎鞋垫、纺棉花、织毛衣,我坐在妈妈身边做作业,在微弱的灯光下成长。
进出房门的时候,我左手握紧椭圆形的灯盏,右手扶着灯罩,小心翼翼,生怕摔坏了灯罩,让灯芯的火苗熄灭,整个屋子就黑灯瞎火了。
当时,煤油按计划供应,供不应求。我们家的房前屋后有自然生长的桐子树和木子树,成为点亮煤油灯的“火源”。春天里,桐子树结出的果子有鹅蛋那么大,木子树结出的果子只有黄豆那么小。母亲把这两种植物结出的果子晒干,到私人办的炼油厂把桐子树、木子树结成的果子炼成植物油,虽不能食用,却可以照明。
母亲为了省下煤油,在棉花搓成的“灯芯”上涂上植物油,用火柴点亮“灯芯”,屋子里亮了起来,虽然没有带有灯罩的煤油灯那么聚光,总比黑灯瞎火强得多。在夏天特别炎热的晚上,我和家人借着月光纳凉,省下煤油和植物油。
读高中的两年期间,我和同学们白天背靠背,聆听老师讲课,晚自习面对面,四个人共用一盏煤油灯。高中毕业这么多年,我和同学们都不会忘记是那一盏盏煤油灯带来的光亮。
去年国庆长假期间,我们高(13)班联谊,叙旧情,拉家常,谈人生。
从十七八岁到六十多岁,跨越了半个世纪,大家再次相聚。我作为此次活动的主持人,讲话时说:“当初我们在上晚自习的时候,四个人围坐在一起,共用一盏煤油灯,你提问,我回答,我报听写,你书写答案,配合十分默契,建立了深厚的同学情。”
来去匆匆,鬓发从黑色变成了白发,脑门上的皱纹依稀可见,最大年龄的同学70岁,最年轻的同学也享受免费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待遇。
岁月的年轮转了一圈又一圈,我们都老了,经历了无数风风雨雨,经历了沧桑巨变,度过了艰难的青春年华。作为一个68岁的退休老人,难忘那盏点亮我青年读书生活的煤油灯。
作者:易先云(68岁)
江汉区前进街道燕马社区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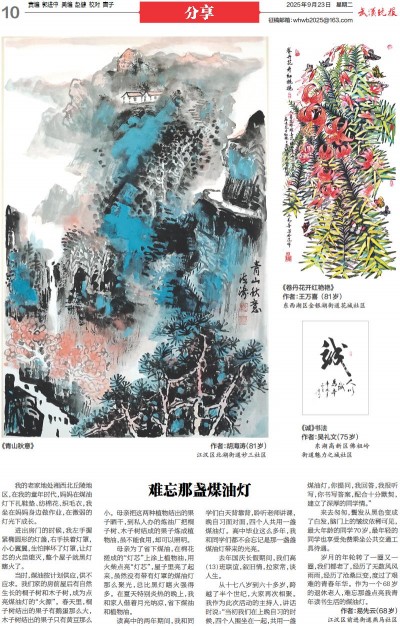

 上一版
上一版



 朗读
朗读 放大
放大 缩小
缩小 全文复制
全文复制 上一篇
上一篇


